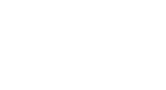梁銘佳畢業於香港大學法律學系,卻選擇了轉戰電影領域,在紐約修讀電影藝術碩士後,專注於獨立電影的攝影工作。他的首部長片為 Anocha Suwichakornpong 的 《看似平凡的故事》,其後作品包括 2015 年張艾嘉的《念念》、2016 年馬楠的《老石》及 Anocha 的《生命宛如幽暗長河》。他在回到香港後,先後擔任《叔·叔》、《濁水漂流》、《白日青春》、《從今以後》和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的攝影。除此以外,他亦曾與妻子 Kate Reilly 聯手執導由 4 段短片組成的電影《夜香·鴛鴦·深水埗》,獲 2021 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編劇獎及推薦電影。梁銘佳無疑是香港電影界不可或缺的一員,其參與的作品屢次備受讚譽,未來他將推出更多令人期待的新作。這次,他與 GQ Hong Kong 分享《地母》的拍攝經歷、得獎感想和對香港電影的看法。
憑《地母》勇奪金馬獎最佳攝影,這是您首次獲此殊榮,當下有什麼感受?回首這一刻,您最想感謝誰?
首先要多謝導演張吉安。他的故事充滿創作空間,包含不同主題:多個種族文化的共存與矛盾、歷史政治的包袱、宗教儀式、人的關係,以及女性與母性在這複雜社會的自處等。但他又不會用太過戲劇化的劇本去說故事,許多事物都是點到即止,亦有許多虛幻但又實在的象徵物。這些都令到視覺創作的過程十分過癮,而不是只在交代劇情、解決問題。他自己本身有很強的 visual sense,非常著重鏡頭的靈性視角,所以我們才可以拍出有趣的作品。

拍攝《地母》時,有什麼難忘經歷?
有好多難忘經歷。因為這製作非常不容易,好像去主場景的路其實是我們鋪出來的,很多場景的製作已經不只是美術,根本就是土木工程。在田裡面走一步,等於在平地走二十步。有幾次在我們剛要拍的時候,雷電就來了,為畫面增加很多氣氛。當然,這也包括演員白潤音哭的一場,架好機位,演員感覺來了,雨也突然來了。牛作為「演員」,也很獨特,我們不能完全控制牠,但在適當時候,牠又會做出意想不到但又合適的事情。這些都令整部電影更有靈性,也讓大自然這個在《地母》裡面的重要角色更加突出。
如何透過影像,進一步表達《地母》的核心訊息與氛圍?
首先要想的,是如何去處理「土地」這個角色。我們希望大家在畫面上看到及感覺到祂的強大:無聲,但又無處不在。我在構圖上一直想強調這點,讓大自然佔據畫面較大比例,以及使用低視角,都是手段。有時人物在畫面上很小,但通過導演的長鏡頭,你又不會錯過,反而感受到人和地之間的關係。「土地」和「大自然」都不是死物,是活的存在,所以有時是攝影機長時間不動來強調大自然的動態,有時是攝影機自己慢慢在動。
燈光方面,因為要貼近鄉間的生活,我可能比平時更注重光的來源,要有當地民間生活的實感,也要和美術一起緊密合作。各種信仰的宗教儀式,又提供了超現實一點的光源,有華麗、神秘、甚至有點荒謬感的紅燈、小火、大火和彩色閃燈。

當地的民俗信仰有沒有吸引你的地方?
這些來自不同文化的信仰,表面上有很不同的對象和內容,我們在拍攝上也有嘗試不同的處理方法,有 overhead tracking 和大搖臂等。但其實這些信仰,不論對象是地母、祖先、大王、又或是陽具,或者布秧谷遺址,祂們都象徵著一種歷史傳承和莊嚴。在不同的拍攝方法上,我們也在尋找一些共通的感覺。

可否講解一下電影攝影崗位的工作和細節,又是如何與各個單位協調?
電影的攝影當然不只是掌控機器。其實,很多攝影指導都不會直接控制機器,基本上要過問畫面內出現的所有東西。由前期開始,攝影和導演就劇本內容討論,去定下電影的調子。討論可以是很具體和技術性;也可以很抽象和概念化;也可以是一邊「睇景」一邊摸索,要配合不同導演與不同的工作方法。攝影師再提出技術上的方法,去實踐電影的世界。拍攝角度、機器移動、畫面質感、燈光氣氛,都是由攝影就他和導演的共識去實現。攝影師與和燈光師溝通,燈光師會就著攝影師的方向去打燈。攝影也要和美術合作,就燈光及色調陳列作判斷;也要就著燈光和畫面,調整演員的走位。
作為導演系出身,同時長期專注攝影工作,您如何看待這兩種角色之間的差異?
導演和攝影的角色有重疊的地方,相對之下導演比較多高層次決定;攝影的則比較多技術上的實踐,但也要就雙方的特質及每一部電影的不同風格和內容而有分別。導演是很辛苦的,所有拍攝決定都由他作最後判決。劇本創作、籌錢、選角、與演員的溝通和拍攝以外的宣傳等等都是攝影師不用管的範圍。相對之下,攝影師的工作比較純粹,要干預的層面都集中在畫面內。我本身讀書時的導演訓練,可能令我更集中於如何用畫面去說導演的故事,而並非純粹畫面上表面的美觀,導演編劇的訓練也幫助我去理解劇本的潛台詞,從中找出視覺創作的養份。

從馬來西亞、泰國、台灣回到香港,你在亞洲各地拍攝多部電影,不同地方的風景帶給你什麼感覺?在拍攝過程中,又有什麼需要調節的地方?
作為攝影師,去不同的地方拍攝是十分刺激的。各個地方的風土人情都會刺激到不同的視覺,既要融入及了解當地人的生活,但亦希望保持外來人的好奇和 critical eye。城市的規劃、鄉郊風景、建築風格、服裝色彩與民間燈光應用,對我這個外來人來說,都可以很新奇,因有時本地人反而會太習以為常。不過更重要的是,當地人的性格民風。在馬來西亞,不同文化共存交雜,所以我會特別留意那裏的不同視覺元素衝撞。在泰國,大家都好像很 chill 很幽默,但 chill 的背後卻有點禪的人生態度,流行通俗的東西卻又可以處理得詩意。台灣總是有點婉若內歛,會令我注意著點點細微的東西。因為中間離開過一段時間,而這個城市一切都在不斷地消失,回到我長大的香港,自自然然令我留意各種情懷舊物,及最平凡最貼身的生活細節。
工作上來說,到不同的地方拍攝,也當然要適應不同的工作文化。很少地方可以和香港的急速節奏相比,這裡的人轉數快,有各種方法解決困難。但有時,冥頑不靈地用死力和耐性去追求一件事,也是很有價值的。老土地說,我都是從不同地方不停學習,交換經驗。

香港電影是一個這麼複雜的議題,您如何看待家鄉的影像創作生態?作為香港人,您最想用鏡頭記錄哪些屬於這座城市的獨特故事?
電影市場艱難,包袱越來越重,越想計算,越不敢冒險。但是,有時就是要冒險,才有新鮮感,而最後,觀眾是希望被驚喜的。拍香港電影,最希望拍出來不像香港電影,但又希望充滿著港味。這聽起來好像十分矛盾。不如這樣說,內容與感情希望捉到香港人的共情;手法與技巧卻希望能跳出香港電影的框架。香港電影很多時感覺上很怕觀眾看不懂,又或者怕觀眾覺得不夠豐富和做得太少。但有時,我們就是想追求曖曖昧昧,留點幻想空間,舉重若輕。

您曾與太太 Kate Reilly 合導《夜香·鴛鴦·深水埗》,可否講述一下背後的靈感來源?有沒有有趣的幕後故事能分享?
我和 Kate 有點大膽地希望《夜香・鴛鴦・深水埗》的原型劇本有點像楊德昌的《一一》。我在 2014 年於外母的家過聖誕時寫完初稿,一個史詩式的大家族故事,志在捕捉當時的香港。回來香港籌備拍攝時,世界一直在變,劇本跟本跟不上。 我們都感到,只有貼近生活的小故事才經得起時間考驗。所以把原型的角色抽出來,變成生活化的短篇,免卻太劇劇化的情節。再加上最貼近當下現實的紀錄片章節,便成為了《夜香・鴛鴦・深水埗》。
其中一幕鹹蛋流心西多,在現實生活中真有其事,但為了畫面效果,我們美術組把裏面的餡料弄得濃一點。 由於鹹蛋流心西多並非我們拍攝現場的原有食物,我們只能用風筒加熱,所以其實十分難食。演員王宗堯吃的時候,其實是冷的。所有吃得津津有味的表情全憑演技。雖然食物是假的,地點也不是真的,但大家都覺得這場戲捕捉到了港味,所以算是我們很滿意的一場。


未來,您是否考慮重返導演崗位?有沒有某個故事類型或主題,是您一直想探索卻尚未實現的?
我自己絕對享受當攝影多於導演,也看有沒有故事靈感吧。如果有的話,我都會想認認真真地拍一些看似很荒謬的故事,但希望「㗳落」又會啓發思考,有餘韻。故事仍是十分空泛,但地點都一定會是香港。
有什麼建議給年輕的電影從業人?
年輕人要有副業,多涉獵一些其他行業範疇,增加人生閲歷,亦能讓電影創作更加純粹。
有什麼日常習慣或愛好,讓您在鏡頭外重拾能量?
鏡頭以外,我喜歡不按食譜去創作一些中西夾雜的菜式,臘腸豉油卡邦尼和腐乳焗羊架之類,有時好好食之後再做不到,有時好難食,不堪回首。但這些都是創作過程的一部份。
Image courtesy of 梁銘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