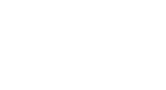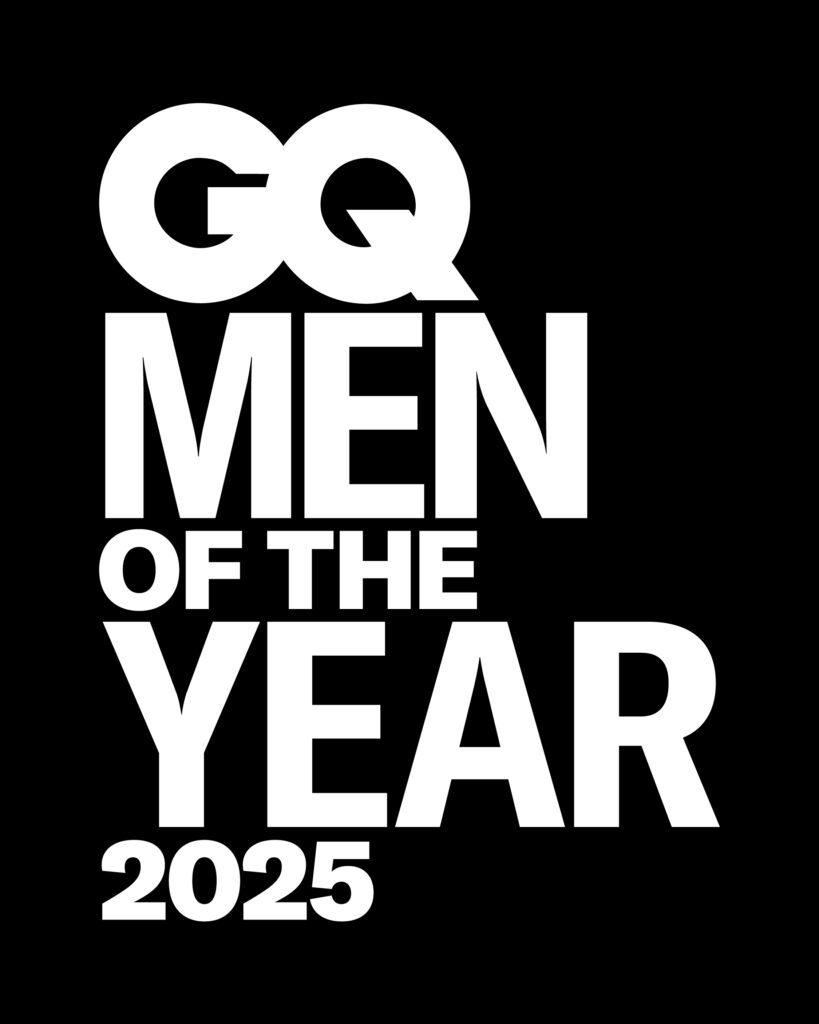銅鑼灣的雪落個不停,紛飛的雪花飄散在熟悉又陌生的香港街道上,彷彿訴說着命運的無常與美麗。
在麥浚龍的電影世界裏,從來沒有純粹的英雄或徹底的惡人。這位身兼歌手、導演與創作人多重身份的藝術家,坐在我們面前,娓娓道來他的創作哲學:「只有在電影的世界裏,才有所謂正角和歹角的明確劃分。」他的眼神中帶着一股近乎執着的堅定:「但在我的電影中,角色往往遊走於大片的灰色地帶,因為我覺得這樣更貼近真實人生。」
八年磨一劍的《風林火山》不僅是 2025 年康城影展的焦點,更是麥浚龍這種灰色美學的極致體現。這部讓金城武、古天樂、劉青雲、梁家輝等巨星以及全港影迷苦候八年的作品,早已成為香港電影界的一個都市傳說。
「真正的浪漫,唯有在悲劇的世界中才能更加突顯。」麥浚龍以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為例,闡釋悲劇如何讓浪漫更顯動人。在他看來,《風林火山》中的角色,無論是所謂的正派或反派,都充滿身不由己的無力感。這種無力感,恰恰映照出當代香港的某種集體情緒。長達八年的製作過程中,香港經歷了疫情與社會運動等巨大變遷。麥浚龍坦言:「拍出來的成品,必須符合不同持份者的要求,也得通過電影審批制度,甚至滿足觀眾的期待,呈現一部能符合眾人期望的作品,這過程極為艱難。」縱是艱難,他也堅持作品必須完成,因為這對他來說,既是一種責任,也是一份使命。
只有在電影的世界裏,才有所謂正角和歹角的明確劃分。但在我的電影中,角色往往遊走於大片的灰色地帶,因為我覺得這樣更貼近真實人生。
《風林火山》的製作歷程,堪稱香港電影史上最曲折的項目之一。劇組甚至搭建了佔地六萬平方呎、一比一的銅鑼灣街景,只為以最完美的方式呈現爆破場面。
在《風林火山》中,麥浚龍刻意將香港這座城市陌生化。他搭建的銅鑼灣街道終年飄雪,香港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煙火氣十足的市井都市,而成為一片被冰雪覆蓋的現代荒原。
「香港這個城市,既有豐厚的人情味,同時也可以極為冷漠。」麥浚龍認為,這種矛盾正是他創作的養分。他不喜歡平鋪直敘地表現香港的地道文化,而是選擇將熟悉的文化符號進行陌生化處理。「例如《風林火山》中的當舖,表面上是典當金錶棉被的尋常店鋪,背後卻進行着買凶殺人的勾當;又比如我們熟悉的銅鑼灣街道,變成終日飄雪、白茫茫一片的陌生死城。」
這種創作手法,使《風林火山》超越了傳統警匪片的框架,成為一部充滿象徵意義的現代寓言。電影中的香港,既是一個具體的城市空間,也是一個承載着人類普遍困境的隱喻舞台。
在麥浚龍的創作哲學中,「留白」佔據着重要地位。他認為:「電影創作應該留有空白,這些空白是讓觀眾自己去想像、去參與創作的地方。」對他而言,這種留白不僅是藝術選擇,更是對觀眾的尊重。「每位觀眾的年紀、經歷與心態各不相同,觀看同一部作品會得出不同的領悟,而這些領悟正是填補空白的方式,讓作品呈現出多元的面貌。」
創作者需要學會抽身、學會放下。當作品完成後,它就擁有自己的生命與命運,即便是創作者本人,也不應再左右其發展。
從當年以歌手身份出道,到執導《殭屍》一鳴驚人,再到歷經八年磨礪的《風林火山》,麥浚龍的創作之路並非一帆風順。然而,如今的他已進入一種更為超然的創作境界。對於下一代年輕創作者,他寄語道:「創作者需要學會抽身、學會放下。當作品完成後,它就擁有自己的生命與命運,即便是創作者本人,也不應再左右其發展。」在麥浚龍看來,作品公諸於世後,無論得到怎樣的評價,創作者都不應過於介懷。「要明白,作品誕生後,它在世上存留的生命,必將比創作者本身更為長久。」
《風林火山》這個片名,取自《孫子兵法》中「其疾如風,其徐如林,侵掠如火,不動如山」的戰術思想。當最後一片雪花在電影中落下,當最後一聲槍響沉寂,麥浚龍留給觀眾的,是一個沒有簡單答案的世界。在這個充滿灰色地帶的香港寓言中,我們看到的不是忠奸分明的傳統敘事,而是每個角色在命運面前的掙扎與選擇。
「我們小時候,首先接觸的往往是一個比較簡單、忠奸分明的世界觀。但長大後,你會明白這樣的二分法在現實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存在。」麥浚龍的作品之所以撼動人心,正是因為他敢於擁抱這種複雜性。
離開採訪間時,麥浚龍的話語仍在腦海中迴盪。或許,《風林火山》無論最終獲得怎樣的評價,都已實現了他的創作初衷——在悲劇的世界中尋找浪漫,在灰色的地帶中發掘人性光輝,在留白的藝術中邀請觀眾共同完成這場關於命運的對話。而銅鑼灣的雪,將在這個由麥浚龍構築的烏托邦中,永遠飄落……
Photography: Ivan Wong
Hair: Powder Ro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