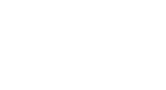在開始之前,我想先問問你對香港的感覺如何?
我愛香港。這是我第一次來到,我真的很喜歡這座城市的布局,喜歡那些有點破舊的歷史建築與新式大廈緊鄰著;喜歡傳統的港口與摩天大樓並存。這對我來說非常有啟發性,或許會做一個以香港為靈感的系列。我非常想深入了解這座城市,或許看看一些這裏的電影。
擔任 YDC 的 VIP 評審感覺如何?
我感到非常榮幸,這讓我意識到品牌已經成長到一定程度,才會被邀請擔任評審。我看到了之前擔任過的名單,包含 Vivienne Westwood 和 Martine Rose 等等,所以我非常感激能名列其中。而且我覺得自己有很多東西可以與參加者們分享,所以我很開心能來這裡提供建議,與他們交談並解答疑問。同時,我也有機會認識全新的年輕設計師,以及他們如何透過設計來看待當今世界,所以我感到非常感激。
在來香港之前,你對香港時尚產業的期望是什麼?
我認為香港非常創新,它擁有許多傳統價值,但同時也擁抱現代性,是一個包容多元文化的旅遊城市。所以我期待看到許多文化拼貼的參照、舊與新的交融、時尚與紡織的創新連結,以及一種源於靠近眾多工廠與行業的工藝性。我對一些設計感到非常驚喜,無論是對性別流動性與性別關係的詮釋,還有對現代世界與科技的探索也非常出色。



談到給年輕參賽者的建議,你認為設計概念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?
我會說是理解事物如何製作而成,工藝非常重要。而且我認為社群非常重要,不僅是養成你的創造力與靈感,還包括品牌建立的執行運作。品牌如何向外溝通?與之合作來傳達訊息的藝術家是誰?是攝影師、造型師、化妝師和髮型師等等,所有這些人,如果他們是你的朋友,或者是你喜歡與之合作來推動自己的人,我認為這會產生某種非常有趣的東西。當我開始時,我的社群令自己的品牌為人所認識,所以我認為複製那個模式也很重要,因為它能幫助你達到你想要的方向。
你如何創立 Charles Jeffrey LOVERBOY? 請告訴我們當時的願景。
我在 Central Saint Martins 畢業後不久創立了自己的品牌。當時的我正在攻讀碩士,但同時我也開始了一個名為 Loverboy 的俱樂部之夜。所以我有點夜生活的名聲,那些有點魯莽且充滿創意的夜晚。我認為那個故事是把我帶入時尚圈的導火線。而且,從那時起,我們就擁抱了品牌中的許多不同元素,像我的蘇格蘭血脈、那裡的傳統格紋、藝術的融入、許多插畫與角色,然後還有性別流動,以及酷兒如何以不同形式表達自己,像男裝與化妝結合的摩擦力。
你如何看待表演藝術與其他形式在時尚中扮演的角色,特別是透過品牌的秀場?
時裝秀是將許多人帶到一個空間去欣賞某種美麗的事物。我參加過許多時裝秀,並且感到非常沉悶,看着人們穿著衣服走下來,在第三或第四個模特兒之後,你就忍不住開始想,這很無聊。所以當我開始做秀時,只是想這是我娛樂觀眾的機會,並展示時尚可以真正成為表達情感與身份的載體。表演是推動這些想法更進一步的絕佳工具。你想讓人們感覺到某種東西,並被感動。我認為像音樂、舞蹈、演戲,或者任何除了步行外的表達形式,是一個絕佳途徑向人們展示你的概念。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處理方法,時尚作為產品、策展或者雕塑,而對我來說,時尚則是作為表演。
系列背後的故事敘述與概念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?
這是將靈感和資料蒐集凝聚在一起的絕佳方式。我認為每一個人都是 storyteller,這是一種人類的共同特質。我們為了處理資訊,透過說故事來明白在不同情況下該做什麼。如果我在思考或感覺某種東西,或者在觀察周圍的世界,我會透過創作某種方法論、故事或世界觀來回應。譬如如果我被 20 年代的風格所啟發,再聽著硬核龐克音樂,如何讓這兩個世界融合在一起?我認為這是關於建構不同靈感能夠共融的世界,也能讓團隊更沉浸和投入。如果團隊裡的人也被故事所吸引,大家一起吸收再創作,生產力也會提高。而且我認為像迪士尼、寵物小精靈與星際大戰的存在是永恆且反常地有創意,因為它們背後有故事與意義在背後,與大眾產生聯繫。例如像山本耀司的品牌創作高度概念性的作品,但他創造的故事總有一個女人與男人貫穿其中。這是一個演變了數十年的故事,一個有幽默感但非常傳統的男人與一個高度挑釁、情感且詩意的女人,那個「故事」應該是更大、更概念性的,或者有時非常簡單,我覺得這些是將人們更帶入品牌的好方法。
你能分享在 LOVERBOY 的創作過程中,一次失敗轉變為突破的時刻嗎?
當 COVID 發生時,我們都隔離在自己的家中。所以,我們必須想出時裝秀以外的方式來發佈造型。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,不過讓我意識到像美術指導、平面設計、印刷與攝影的力量。之前,我們只是把這些視為用於行銷的外部產物,但實際上它們亦是能傳遞品牌美學的藝術表達。我們與 Tim Walker 做了一個項目,達到非常成功的效果。跟隨那時做了盒子秀的 Jonathan Anderson,我們不斷在思考使用平面媒介的各種方式,來讓人們體驗我們的品牌。


如果 LOVERBOY 要與一個完全不同媒介的藝術家合作,你會選擇誰,以及你會創造什麼?
我一直想與影像創作者 Chris Cunningham 合作。他與 Aphex Twin、Björk 這些偉大的音樂人經常合作,而且因在 90 年代製作非常進取的音樂錄影帶而聞名。我透過樂團 The Horrors 發現他的作品,他為歌曲《Sheena Is a Parasite》做了這個驚人的影像,我從未如此感動,如此有攻擊性像在直接對我靈魂說話。而且他的創作過程總是透過某種聯覺方法,聆聽要做音樂錄影帶的歌曲,並將音樂的每一個位元與一個圖像相關聯,令成果與聲音完全一致。我很想和他製作與我的品牌相關的作品。

你是否將情感脆弱用作時尚敘述的工具?
當我在製作系列時,總是將設計回到我的核心情緒,無論是對世界政治議題的反應,或者是作為正在老去的同性戀者的感受。這些感覺絕對被投放進我的作品。你可以慢慢建構出代表那個隱喻的資料蒐集,但如果我領導一個團隊並關注著當中發展,最終我需要引導他們去需要去的地方,這些核心起點就像是系列的北極星。雖然我們都是不同的人,但我們都是人類,都能產生共鳴。我們都會有像悲傷或憤怒或熱情,或者興奮的感覺,從而對其他人如何感覺某些東西感興趣,學習並身同感受。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喜歡看電影或讀書,即使不是同樣的故事或經驗,但總有某種能在情感層面產生共鳴的東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