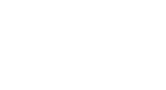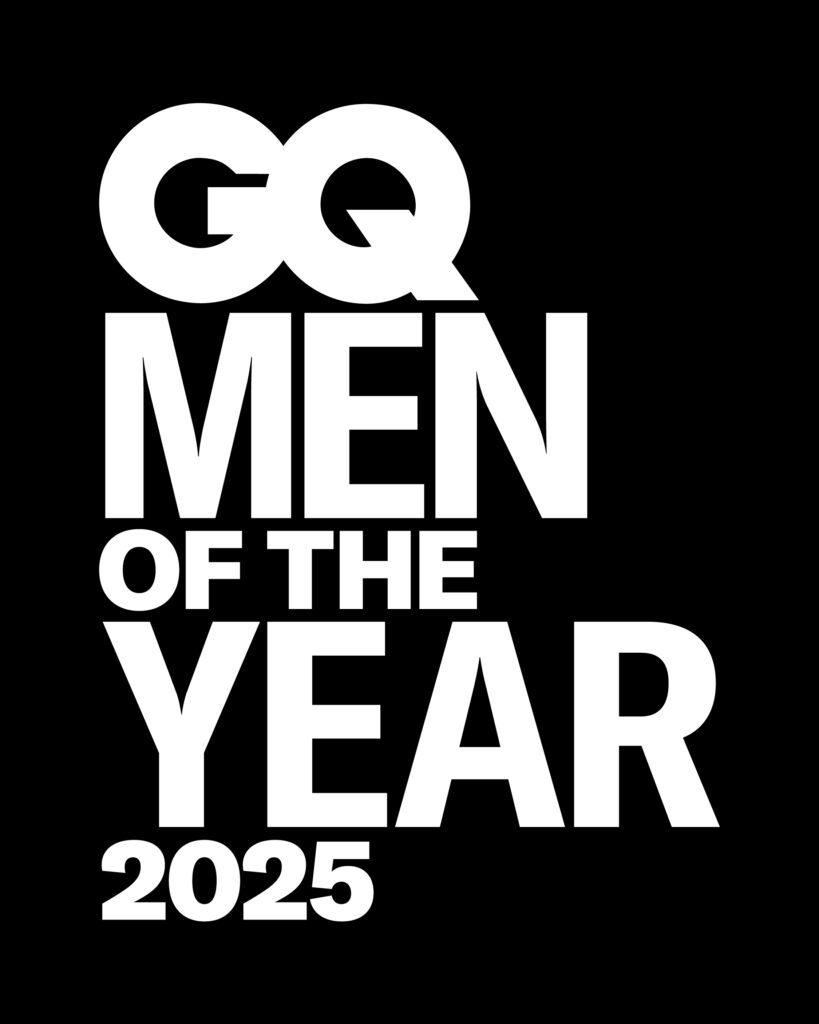「小時候心目中第一個香港英雄,一定是李小龍。」文念中坐在他位於大角咀的工作室裏,窗外層層疊疊的新舊建築交織出香港獨有的天際線。他的聲音溫和而堅定,談起李小龍這位傳奇人物時,眼中閃爍着崇敬的光芒。「他將香港帶到國際舞台,讓世界認識這個彈丸之地。他破舊立新,融合傳統武術與個人哲學,轉化出全新的東西。」這種破舊立新的精神,不知不覺間成為文念中美學道路上的指南針。
「我很期待,可否做一些不被期待的事?」文念中笑着闡述他的創作哲學。在電影美術的世界裏,他總在思考:能否打破那些看不見的框架?這種突破,在《花樣年華》中得到了完美體現。作為該片的美術及服裝設計之一,他協助張叔平打造出那個充滿 60 年代風情的香港—花牆紙、花布傢俬、旗袍女子的婀娜身影。電影成功後,這種美學風格驚豔世界,讓全球觀眾為東方美學的獨特魅力傾倒。
然而弔詭的是,成功反而成為他急欲擺脫的桎梏。「完成《花樣年華》後,許多電影都紛紛借鑒這種風格。」文念中回憶道:「那段時間我反而很抗拒,刻意避免回到那種美學路線。」這種自覺的規避,正是他破舊立新精神的體現—不願耽溺於成功的舒適區,而是不斷追尋新的可能性。
從入行開始,無論是年代片還是科幻片,都需要進行資料搜集與研究,這過程中,我一點一滴地建構起對這個城市的認知。與其說是沉重的使命,對我而言這從來都是件很有趣和快活的事。
文念中的作品橫跨不同時代,從復古懷舊到未來科幻,他的美術設計不僅記錄了香港的風貌,更融入了對這座城市的想像。當被問及是否自覺肩負記錄香港視覺歷史的使命時,他謙遜地搖頭:「我不敢說是使命。從入行開始,無論是年代片還是科幻片,都需要進行資料搜集與研究,這過程中,我一點一滴地建構起對這個城市的認知。與其說是沉重的使命,對我而言這從來都是件很有趣和快活的事。」
對文念中來說,創作既是對過去的追溯,也是對未來的預測。無論是重現一個時代的質感,還是構建一個科幻的香港,他都以謹慎認真的態度進行大量資料搜集與深入研究。儘管他輕描淡寫地否認了「使命」一詞,但他多年來的美術指導工作,無形中已為這座城市不同年代的美學留下了珍貴的視覺印記。
談及何謂「香港美學」,文念中的眼神變得深邃。他認為香港的特色在於中西文化交融與高密度的城市肌理。然而在這高度密集的都市中,他反而追求「留白」—在緊湊的城市風景中尋找呼吸的縫隙,於畫面中為觀眾保留想像的空間。
這一代年輕人,要麼躺平,要麼就充滿想法和行動力;屬於後者那派,根本不需要別人給予甚麼寄語,他們完全有能力自己克服困難。
文念中憶述童年時的香港街道:「小時候放學坐校車經過這些小街,覺得這座城市真的很美,宛如身處遊樂場。沿街可見各式店舖招牌,上面那些中英文字排列看似雜亂無章,卻有着亂中有序的獨特美感。」那是個充滿色香味的城市,既有視覺上的五光十色,也有大排檔的香氣裊裊。這種多感官的城市體驗,深深影響了他的美術設計。在他的作品中,我們總能感受到香港不僅是視覺存在,更是能觸動所有感官的有機生命體。
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創作人,文念中對年輕一代創作者充滿欣賞與信任。他坦言:「我不敢說有甚麼寄語給他們,現在的年輕人都很厲害。科技發達讓協助創作的軟件和硬件都普及化了,他們有屬於這個時代的解決方法。」他拒絕以前輩姿態指導他人,而是選擇以合作者身份,與年輕人共同探索最適合當下的創作路徑。「這一代年輕人,要麼躺平,要麼就充滿想法和行動力;屬於後者那派,根本不需要別人給予甚麼寄語,他們完全有能力自己克服困難。」文念中笑着說。
從《花樣年華》的懷舊美學,到《好好拍電影》的記錄真實,文念中始終在追尋香港美學的多元面貌。他的作品告訴我們,香港美學不僅是視覺風格,更是一種精神態度,在傳統中創新,在限制中創造,在狹小空間中開拓無限可能。這種美學態度,或許正是香港精神的縮影—在彈丸之地上創造奇蹟,在東西交匯處找到自己的聲音。
這或許就是文念中作為香港英雄的意義—不必改變世界,而是透過美學,讓世界看見香港的獨特與美麗。在破舊立新之間,找到屬於這座城市的美學語言,並將這種語言,帶向更遠的遠方。
Photography: Ivan Wong
Styling: Kyle Tang
Make up & hair: Constance Chan
Wardrobe: Berlut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