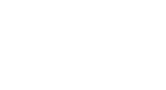CJ Hendry 大學時修讀建築及金融學系,輟學期間拿起畫筆開始素描並在社交平台分享,其幾可亂真的超寫實畫作,吸引到超過 92 萬粉絲,同時吸引到 Kanye West 和 Vera Wang 等名人收藏。CJ Hendry 在 2013 年輟學,短短一年時間,即有一幅黑白靴子素描以 1 萬美元成交,作為從沒受過正式藝術訓練,只在社交平台分享畫作的創作者,這一宗成交無疑為她爭取到投身藝術界的入場券,而快閃展覽中的 Juju 素描成交價早已超過 45 萬美金。

CJ Hendry 坦言:「我覺得自己不屬於藝術界,沒有上過藝術學校,也沒有接受過正式的藝術訓練。對我想說,選擇超寫實主義是因為這是我唯一會做的事情,因為我並不知道怎樣畫畫,也不會做抽象的東西。超寫實風格就不太需要創意,它是一種 craftmanship,只要你能夠坐下來、長時間專注就是了。我很喜歡繪畫帶給我的感覺,它能讓人沉澱,將注意力集中於筆尖與紙張,忘記身外事,帶有冥想的特質。」


消費主義一直是她創作的核心,大學期間她在名店當兼職售貨員,把所有沉迷於購買各式各樣的根本負擔不起的奢侈品,直至多年來的過度消費讓她銀行帳戶空空如也,就在那一刻,她突然頓悟。 「我想,我肯定能有比這更好的成就吧?」她開始繪畫,而她最初的作品都是以奢侈品為主角,黑白素描的 CHANEL 紙袋、Dior 絲巾、Christian Louboutin 波鞋等。

其中一幅以 Kanye West 頭像代替富蘭克林的 $100 美金素描,更被本尊收購而成為佳話。但她指,金錢並不是她的動力。「剛開始時根本賺不到錢。我沒有想到過如何賺錢,目標一直都是做藝術並提出有趣的想法而已,我相信只要你的想法夠出色,金錢便會隨之而來。」


的確,CJ Hendry 在社交平台上收獲了大批粉絲,她的平面畫作亦演變為沉浸式裝置,展覽如 《Monochrome》(2018 年)、《Blonde》(2021 年)和 《Flower Market》(2024 年),將藝術與互動體驗融為一體。「我記得在大約 5 年前,我對繪畫越來越感到沮喪,因為覺得 2D 畫作相當有限。它只是一張紙,而且賣得非常貴,作品也只會收藏於買家的家中。我希望能夠表達和分享更多創意,渴望建立更大的實體概念,一些可以讓人親自走進去、或觸摸得到的東西。」

品牌如 Christian Louboutin 在 2017 年與 CJ Hendry 合作,在香港的藝術巴塞展會中,將鞋履與畫作聯乘展出;2023 年與 Phillips Auction House 推出的 Crown 系列,同時為拍賣行的 Dropshop 平台開辟了新局;2024 年在沙漠中設置的 Public Pool 裝置⋯⋯都一一實踐了她的創作理念。


CJ Hendry 的最新創作是玩具作品 Juju,再次與 Phillips Auction House 合作,於亞洲總部作快閃展覽,陳列設計模仿超級市場,還有雕塑以及 Juju 本身的超寫實畫作、毛絨玩具盲盒等。Juju 的出現正如她對自己創作生涯的總結一樣:「從來不是故意規劃,一切就像意外般發生的。」年初,Phillips Auction House 表示希望再次與她合作。「他們問我,有聽說過 Crybaby 嗎?有聽說過 Labubu 嗎?他們鼓勵我從這個方向考慮,而我當時根本不知道對方在說甚麼。後來,我開始上網搜尋這些潮流玩具的資料、認識盲盒熱潮⋯⋯到最後,我就想:『我們來做一個玩具吧。』」

CJ Hendry 當時甚至不知從何入手,她使用了 AI 工具如 ChatGPT 來進行設計,經過多次優化、改進,漫長的 11 個月時間,最終有了 Juju——一個有着垂下來的耳朵、花卉覆蓋眼睛的毛絨玩偶,在展覽期間以盲盒形式發售。「如果有人說,Juju 跟 Labubu 很相似,我會很高興,因為這正是重點。作為一位藝術家,我要創造的,正是這種對話與藝術的反思。」


Juju 再一次以消費主義探討了盲盒熱潮,而 CJ Hendry 在回應盲盒熱潮這個議題時,同時亦堅持以最高的質量去完成所有細節,例如以客製化的金屬罐取代紙盒、每一隻玩偶都以她的家人好友命名⋯⋯觀乎展覽開幕當天,開門前早早到場排隊的粉絲,抑或是在「超市貨架」上搜購心頭好的玩具收藏家,「買家」即場「開箱」、與在場互不相識的人們交換心儀的玩偶,這種社群的互動、接觸是 CJ Hendry 作為藝術家更珍視的一環。

在拍賣行這種向來標誌着高價藝術品的殿堂場所,Juju 系列卻同時擺設 $188 的盲盒與超過 300 萬的畫作同場開售,本身已是一場對藝術體制的叛逆宣言。Juju 的高低價差,將藝術的門檻撕開一道裂口,幾那種「可望而不可及」的藝術品消費從雲端拉回地面,讓藝術真正與日常生活融合。